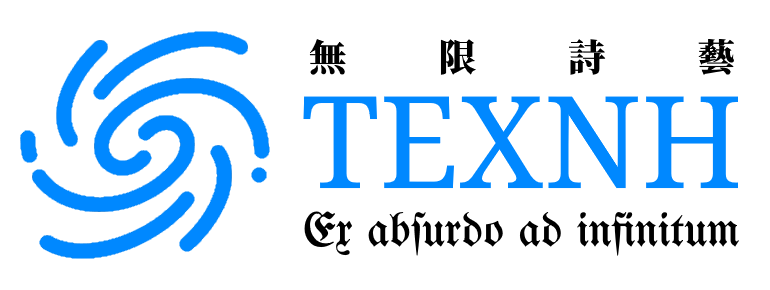故园
这是在哪里?很好。这回真的看不出来了。
刚才有个倒霉鬼宣称自己不看显示器的模拟图像就能正确导航,现在的情况应该已经足够让她后悔,如果她还能后悔的话。
周围很黑。我猜测我们可能已经着陆了。
我想起不久前我们还在做着陆的准备,在进入程序的时候,整个船体突然摇晃起来。在我意识到应该确认一下当前的位置时,不知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中间可能还做了一个梦,然而现在已经什么都想不起来。
视野渐渐恢复,照明仍然不足。努力维持工作的只有舱内应急设备的指示灯,勉强能给出周围物体的轮廓。
我注意到有一个红色的小灯,它的位置让我有点紧张。任务手册里在描述这个红灯的时候还特别在文字旁边配了一个有感叹号的黄色三角形图标。我一直以为如此认真严肃地描述一个在我们的时代近乎内化到本能中的危险感觉是很尴尬的事,没想到有朝一日真的要面对这种最为经典的灾难。
船漏气了。
尽管离真正构成威胁还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强迫自己立即爬出座位去检查一下情况。这里的空气不是完全不能呼吸,只是里面含有一定比例的致幻成分,具有类似某种花的香味,过量吸入才会导致昏迷和死亡,这比直接要人一命呜呼更让我恶心。
什么鬼地方!我至今无法清楚地论证自己为何而来。有趣的是,即便如此我还是通过了选拔,这使我怀疑这个号称满载人类希望的项目实际上是应者寥寥。或许真的只有足够绝望的人才会选择一个如此彻底地重新开始的机会。
计划中这个星球的名称为Kowen。我有自信认为当时选取这样一个充满日(恶)式(臭)暧(修)昧(辞)的名字是出于纯粹的恶趣味。先不考虑正字法的问题,单是字面的解释就有许多可能。我个人倾向于理解成“故园”或者至少也是“古园”,而另一侧陷入变形船体中应该已经死掉了的可怜女士则认为是“孤园”。“公园”这种异端的支持者也是有的,谢天谢地,他们没有跟我们一起来。
是的,我刚才转头确认了一下她座位附近的情况,有一股腥味。我知道这一切不是她的错,她只是说说而已,但我也不想再管她了。失去一个有趣的同事的确令人难过,但事实就是事实,拒绝它不会有任何好处。再见吧,倒霉的人!祝你好运,并且被导航去你该去的地方。
爬出座位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的头和脚都很痛,虽然应该没有伤筋动骨,但十分影响用力。要是再多些船员就好了,这种时候至少可以互相帮助。只有两名队员的探险队简直不可理喻,我不知道对那些人而言这个计划究竟是什么意义。不过因此也就可以确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情况确实不妙。任务已经失败,可以说是没有挽救的必要了。存放设备和物资的舱室整个脱离,如果先前的摇晃是因此产生,那么我们丢失它的时间点未免也太早,说不定它现在还在轨道上飞呢。我的心情意外地平静,或许是因为只有这一点是意料之外。一个绝望的人是不会感到更绝望的。
差点忘了。船舱的一侧裂开了一个可怕的大缝,把手贴近隐隐约约能感受到气流。赶在闻到那种香气之前我就奋不顾身地扑向存放备用维生设备的柜子,取出空气罐,接上面罩,一气呵成。这一套动作加剧了头和脚的疼痛,我有些后悔,这样着急似乎并不值得。
我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根据原定计划,我们要利用那些设备和物资建立一个实验性的长期居住环境,并且获取有关这个星球一切可能的数据发回。如果地球方面判定可行,之后就会派更多的人来。看起来是非常稳重的方案。然而这艘船已经连通信设备也无法工作,它完全聋了,永远沉默了,他们不会得到更多的回复,所以也就是死了。我其实也一样。不过想到在正式死亡之后还能活上一段时间,实在是有些愉快。这是真正的奖赏。
另一个令人愉快的原因是,我发现在这里并不是绝对的只有一个人,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相见。这使得某个企图通过命名决定现实的努力完全白费,而她差一点就能得逞!哦,对不起。这里完全不必是“孤园”,我找到了一个便携式录音机,我想一直开着它,直到它的电池或者储存空间用完为止。任何捡到它的人都可以获得由我送出的奖赏。我觉得这样很平衡,平衡是这种处境下最珍贵的美德。
让我想想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停留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不想继续陪她。千里迢迢来到这个星球,我对自己意外取得的游客身份相当满意。而且我可以确信,我完全实现了这样一种境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确实是我的审美品位,或者应该说,这就是我应得的。此时作出任何前进的决定都是配得上我的高贵行为。
就像是为一个人的郊游做准备,这种计划一点也不让人苦恼,尤其是完全不必自己准备食物时,而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连选择决定的步骤都可以省掉。我又打开了刚才的那个柜子。根据手册中的说明,这里应该还预备有一天所需的食物和水。他们没有骗我,这些都放在一个背包里。
我现在终于可以大胆地公开承认,其实不久前我弄丢了任务手册。这件事不符合我的一贯作风,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提,也没再去要一份。众所周知,大概只有编写手册的人才会以顶级辩护律师的严谨态度审阅它,而且到了真的出现某种问题需要查阅确认时往往已经无济于事。我很幸运,我是那些律师的知音。危机处理这一章节可谓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阅读的乐趣堪比在捉襟见肘的法律条文中钻出漏洞。我只读这一章,我享受作为征服者的过程,乐于见它出丑,尽管很难说我同样能够如此征服眼前的窘境,并且它很快就要没用了。出丑的可能是我。
按照标准流程,确认身上的防护服,把面罩换成头盔,空气罐和录音机放进背包,把它们连接到头盔并配置好,背上背包,然后忘记标准流程,直接打开逃生门。
我的头好像不怎么痛了,可能这只是因为我更多地关心我的脚。逃生门的结构有点损坏,根本不能优雅地打开,我最后用的是脚。我没有蠢到用疑似受伤的脚去踢门,然而在这过程中它还是受了很多力。令人欣慰,逃生门损坏的程度足够。
我向前迈出第一步。这是我个人的一次小小郊游,和全人类没有一点关系。防护服内我无法感受到风,可我还是感到一阵无形的风扑面而来。如果风是一种信号,我应该是见识到了最强烈的表达欲望,尽管其含义隐藏在不可理解的形式背后。踩在坚实的土地上,这种感觉简直和在地球上一模一样。
我反应过来,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这意味着我们之前所作的长途旅行可能根本就是原地打转。这次任务可能根本就是一个骗局。这个星球可能根本就是……还是早点放弃吧。这种阴谋论固然增加了事件的戏剧性,但同时也使得我从一开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显得无比荒诞。我为什么要来地球——不,“故园”?然而这种逃避也显得无力。我向来畏惧文字游戏的谶语,我参加这个项目可从来不是为了回家。确实,我无法说明为什么要来,可我是一定不能不来。我必须在完全失去容身之所前体面地去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来证明我并非被放逐,而是自由地选择了将来的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应该感谢他们把我送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我敢保证与地球如此相似的星球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暂且不提这诡异的空气,我对这里的重力、气温、大气活动、昼夜长短、日照强度等等都相当满意,对于一个死人而言堪称奢侈,而我现在就可以见证这一点,这成功地把我从危险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天蒙蒙亮,应该还是日出之前,虽然感觉颜色不太对,有点偏绿?无所谓。这天光正适合出发去郊游。我后悔了,我本应该再要一份任务手册的,里面有潜在着陆地点附近的详细地形图。我发现我们坠毁的地点在山谷中间,好在两侧的斜坡都比较平缓,先登上山顶或至少是高处再作打算显然是明智之举。
我的脚很快向我报警,我低估了这次郊游的严肃程度。周围除了大块的岩石就只有小块的细碎的岩石,看似平坦的地面其实无比崎岖,每走一步都像是按动疼痛的开关。我没有理由过多地担心已经作为消耗品的肉体,可是脚上的疼痛正在扩大,甚至成为头不再疼痛的原因,并与周围无聊透顶的景致一同企图毁掉我的心情。
要是这里有些别的什么就好了。
我曾经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登山,山路是同样的崎岖,甚至有时更糟糕。但那时每走一步,周围植被或岩石的相对位置就会因为层次关系而发生变化,使得不同的细节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眼帘。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可以创造出无数种绝不重复的审美体验,自然也就不会使人厌倦。我至今还能记得当时山上盛开着一种天蓝色的小花。一开始它只是零星地分布在山路两侧,而且因为实在是太小,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直到从某个时刻起它们开始成群地生长,我立即被它们纯净的颜色吸引了。我以为这些花儿就是为我而开的,它们聚集在一起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而我并不通晓花的语言。不过当我经过一个拐角,看到它们不遗余力不留空隙地倾泻在整片山坡上时,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空和大海的全部奥秘。然后我就下了决心,报名参加这个项目。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日光还原了周围景物的真实面貌。黑色和白色混杂出一种不纯的灰色,把大地模糊成一块不可分隔的整体,不仅使人厌倦,有时还教人反胃。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不少路程,而到所谓的山顶的距离似乎丝毫没有缩短。
我现在更希望回到从前。我不是说回到从地球启程之前,而是着陆程序开始之前。我当时应该手动操作接管飞船,调转方向去往无限的未知,而不是乖乖降落到这个地方。我们有足够的物资和能源,我们还有人,丢掉一些没用的设备我们还能有足够的空间。我可以设想一百种比现在更为快乐的生活方式,我还可以活得更久。这种决定当然同样与我相称,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不会那样做的。
我必须前进。我不愿发现脚上的疼痛已经蔓延到整条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任何逻辑的解释都毫无必要。任务手册中不会对这种事有任何提及。我只知道,只要多迈出一步,我就能向前更进一步,保持平衡,顺势用另一条腿再迈一步,节约体力,循环不停,然后忘记这一切。
我很擅长面对外部世界,并且引以为傲。我出生于十八世纪的一个牧师家庭,因天资聪颖受到资助去往神学院学习。如果一切顺利,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之后,我就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然而不幸的是,我天生拥有诗人的本质,我遭遇了魔鬼的诱惑,或者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沉迷于解释学的利刃,以此击破世界的表象,从而远离了神圣的庇护。生活在不经修饰的真理之中需要一些技巧,经历无数的苦难之后这总是能学会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安娜,我向她求助,经她的介绍,我获得了一份土地测量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大致稳定,可我的心不幸已经败坏了,几个月后我就发现比起测量大地,我更愿意创造大地。我熟知世界运行所必需的每一个象征、每一种联系。我在模拟软件中调试了很久,按照自己的喜好设计了一切细节,让所有的重担都被减轻,最后把成品的模型公开到全部网络。我提交的土地测量数据甚至有一部分就来源于此。我没能收到任何感谢,因为人们都已经深陷其中。
无人能够抵御无条件的爱,这就是我的犯罪,我的僭越。我并不是要通过自虐来赎罪。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其中包括选择自己承受自由或者把自由交付他人的自由。但如果是处在某种非常特殊的立场,这种对自由的描述也就不适用了。因此,我相信同我一样走到这里的人至少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与我意见一致,至于附加条件我自然不会强求。
太阳升高了,光线非常刺眼,地面的反射也相当强烈,几乎使人无法直视任何东西。内部的空气变得闷热,想要避免中暑就必须取下头盔。我很疲劳,前进的速度明显变慢。地面坡度似乎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成功的幻觉,这样可疑的事情倒是非常讽刺地契合我设计的算法。我不在乎,我当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登上山顶,我只是向前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就这么简单。我感到口渴,我感到饥饿,但水和食物并非完全必要,我不依靠它们活下去,只是这个头盔我必须丢掉了。好吧,我接受任何嘲讽,我可能很久以前就热得把它丢掉了,这毕竟是在运动。
我不是一个善变的人,但我似乎开始愿意恢复对这个地方的赞美。我只有空手来到这里,才能让奇迹有机会发生。
让我谈谈希望吧,眼下已经适合谈这个了。如果可以祈祷许愿,我还是很想再见安娜一面。中学时我就与她相识,她知道我的所有事情。每当我感到痛苦难以忍受,我就去她常住的山间小屋那里,她总是能使我恢复平静。她理解我,我有时能理解她,有时不能。
这种环境就是有这样的作用,我无法停止想起曾经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最使我耿耿于怀的,还是我从来都没法想像她的容貌举止。只有她在场,我才能发现并确信自己与她熟识。这应该是唯一能成功阻止我来的理由。好在我觉得她也和我一起来了,我对她说过,她是知道我要来的。
一阵微风吹过,我顿时满怀感激。我的腿已经毫无知觉,我甚至看不见它们,同理路也渐渐平坦起来,我应该为此高兴。我的脚步轻快,穿过零星点缀的花花草草,看到它们不断地茂盛、丰富,驱散一切可见的荒芜。我第一次感受到周围风景的优美,我明确预感到会有好事发生。
前面就是一个熟悉的拐角,经过它,去山石的背后。从天空和大海中,一个人影向我走来,是一位身穿舱内便服的年轻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看起来相当可爱。她的头和脚上有一些血迹。我也向她走过去。我对她打招呼。她只是看着我,微笑,却没有任何深意。我上前想帮她清理一下,她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我轻轻抓住,跟随她,越过天空和大海,去往彼岸的一间小屋。我好像知道她是谁,我觉得应该跟她去。我感到无比欣慰,这故园的确是与我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