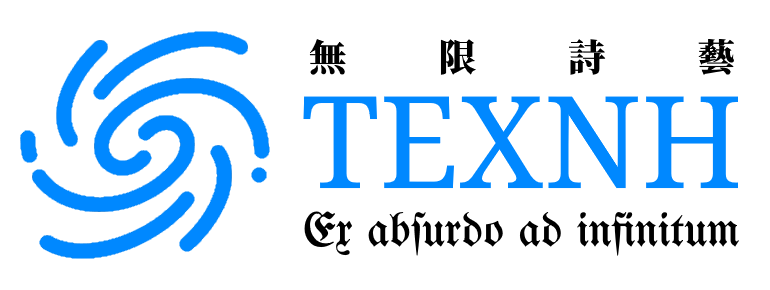追问生命的意义
当我们的生存方式被一再追问后,便不必再解释我们的存在是有多么地荒诞。面对这样一个虚无的世界,我们感到压抑,或者恶心。不是因为某些条条框框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过多的自由但没有能力承受,因此,我们在决定自己的存在方式时感到无从下手。
作为手段的道德是空虚的,是不可证的,是人用于自我欺骗的理由。借助道德,我们能够做出许多被合理化了的选择。一些看似可以用作建立道德的基石的原理,其实从未被认真地审视过。它们一旦被追问,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整一座道德大厦的崩塌。理性主义的胜利,就是这一进程的加速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理性的需要,又有新的上帝被树立起来。
上帝本无过,上帝的失误实际上就是人的失误。人所能塑造的最完美的事物就是上帝,同时人也分享着神性。这就意味着哪怕是上帝这样的客观精神的指导都是相对的。而从相对的事物中又怎样才能发现永恒的真理?我们必须追问前提。
于是我们不断地追问真理背后的真理。作为个人的行为必然符合生命的意义,作为生命的意义必然寓于宇宙的意义中,“人生界”与“宇宙界”的根本隔离既然不存在,我们便可将希望寄于某个终极真理上。使用逻辑技巧固然可以作弊得到某个答案,但这样做无异于承认逻辑的绝对完美,照样能被追问。人类“知其不可而为之”,所有的人都在这条路上执着地前进。人类便欣喜若狂地认为这种过程就是生命的意义。
可是,我又可以追问,“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真的存在吗?“42”真的可以决定地推出“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吗?
我们世界的根基,真的是形而上的吗?
近年来的物理学研究渐渐浮现出佛教的特性,莫非为人所骄傲的理性也将走到尽头?编写我们初中科学书的朱清时老师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听见传唱不息的经文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缘起性空,何须执着?